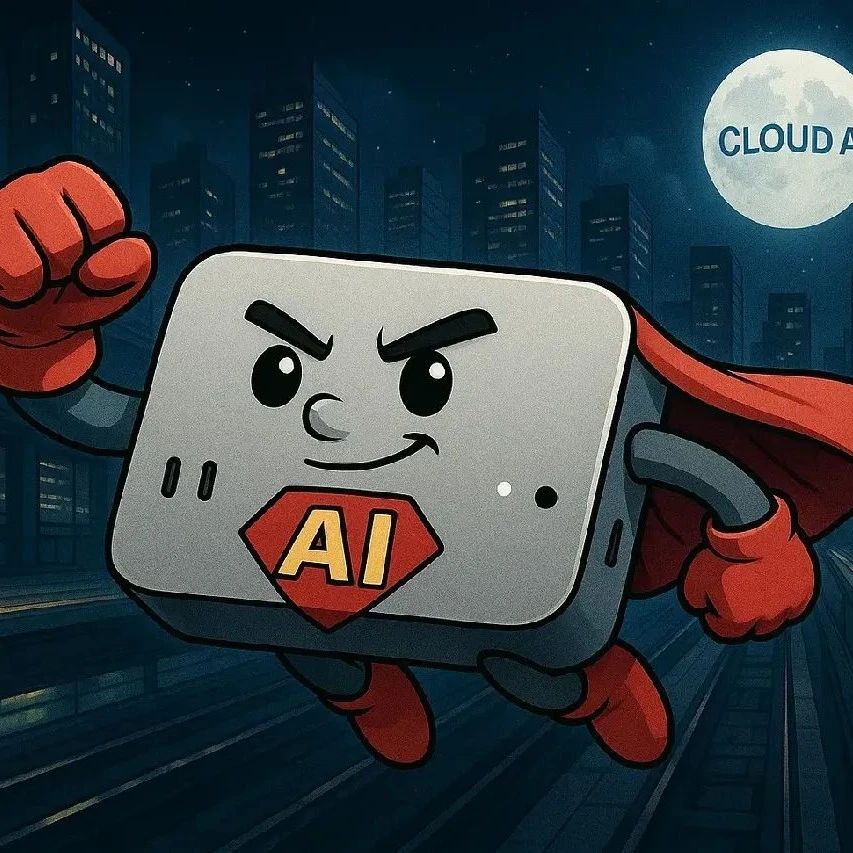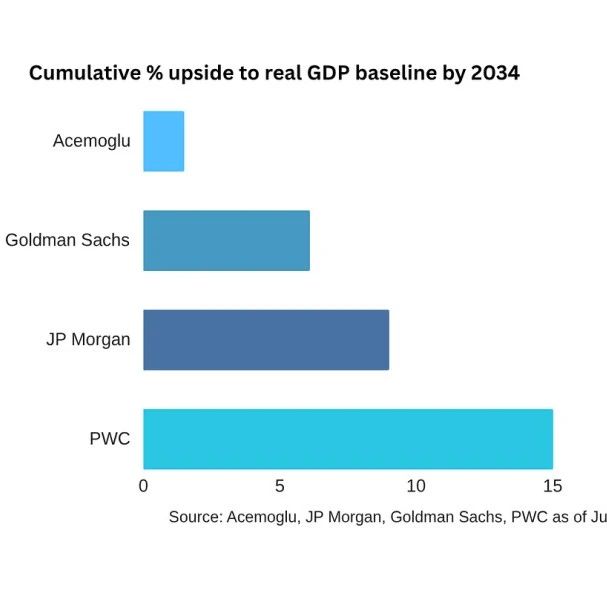我们如何一步步教会机器思考?从莱布尼茨到图灵,一部贯穿 300 年的 AI 史诗,两次寒冬、三次浪潮,最终走向何方?
- 2025-07-23 18:29:46
注意:本文内容源自正在创作的书籍《基本无害的 AI》。该书旨在探讨如何驾驭人工智能以造福人类。
作者:ALEJANDRO PIAD MORFFIS
日期:2025 年 7 月 22 日
数个世纪以来,人类始终对一个疯狂的念头深深着迷:一台会思考的机器。
这并非现代科技热潮的产物,尽管今天这个话题无处不在。这个古老的梦想源远流长,早在神话传说中就已悄然流传。
人工智能的历史,最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,便是在两种核心且看似对立的路径之间,反复上演的戏剧性博弈。
一方是逻辑与规则,即所谓的符号 AI;另一方是数据与模式,也就是统计 AI。
这在深层次上,恰好映射了哲学领域那场旷日持久的思辨:理性主义,通过纯粹推理探索世界;与经验主义,从感官经验中获得真知。
本文将以理性主义(符号 AI)对抗经验主义(统计 AI)的视角,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。
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索,看这对看似对立的哲学思想,如何塑造了 AI 的过去,定义了它的现在,并最终开始携手,共创它的未来。

序章
人工智能的梦想,并非始于硅谷的芯片或代码。它的起点要早得多,源自宏大的哲学抱负与极富想象力的智慧飞跃。
这一切,都要归功于那些才华横溢、思想多元的先驱。
我们的旅程从 17 世纪的戈特弗里德·威廉·莱布尼茨开始。在当时,他已是哲学、数学、逻辑学和外交领域的超级巨星,并独立于牛顿发明了微积分。
我们今天使用的微积分符号体系,很大程度上正是他的创造。
莱布尼茨是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,他毕生致力于将所有知识与理性系统化。他坚信,逻辑足以平息人类的一切纷争。
他梦想着一个不再需要争吵辩论,仅凭冷静计算即可化解分歧的世界。
代数与微积分能用简洁的符号化解复杂难题,这深深启发了他。在一个连简单计算器都堪称奇迹的年代,他燃起了对通用计算的宏伟愿景。
他构想,是否能将所有人类的推理过程都进行形式化表达?他梦想创造一种通用的思想语言,以及一套可与之匹配的机械推理演算系统。
莱布尼茨是一位彻底的理性主义者,他相信人类思想本质上是一台宏伟的逻辑机器。不经意间,他为数百年后的符号 AI 奠定了思想基石。
时间快进到 19 世纪的英格兰,我们遇见了埃达·洛夫莱斯。
作为著名诗人拜伦勋爵的女儿,埃达拥有非凡的才智,在当时最顶尖学者的指导下研习数学与科学。
她与伟大的发明家查尔斯·巴贝奇相遇时,后者正致力于打造他的分析机——一台理论上能完成现代计算机一切任务的抽象机器。
埃达不仅以其敏锐的思维和惊人的数学洞察力闻名,更将一种诗意的想象力注入了她对技术的理解中。
巴贝奇主要将分析机视为一台终极的数字运算工具,而埃达的思绪早已超越了算术的边界。
她曾写下著名的预言:分析机或许能创作精妙的科学乐曲,或在任何领域生成全新的内容。
她比生成式 AI 的诞生早了一个多世纪,已经开始梦想机器将开启一个合成创造的新纪元。
值得一提的是,巴贝奇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分析机的实体建造。他沉迷于无休止的改进,使其永远停留在了图纸阶段。
这台本可成为世界首台计算机的机器,最终沦为一个警示。后人将其称为巴贝奇综合征:无休止地进行思想推演,却从不付诸实践。
又过了几十年,20 世纪中叶,战争的硝烟散去,数字时代的曙光初现。
计算机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——伟大的艾伦·图灵——登上了历史舞台。当他关于机器智能的开创性论文发表时,他早已是公认的顶尖逻辑学家与数学家。
他提出了图灵机这一抽象计算模型,为所有现代计算机提供了理论蓝图,堪称计算机科学之父。
他在战时破解德军“恩尼格玛”密码机的经历,让他对计算的力量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。
事实上,他亲手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机电式通用计算机,但这一伟大成就,直到他去世多年后才得以公之于众。
图灵是一位沉静而才华横溢的思想家。他不仅探索机器的能力边界,更从根本上叩问思考本身的定义。
在他 1950 年的传世之作《计算机器与智能》中,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问题:机器,真的能思考吗?
他设计了一个巧妙而深刻的测试方法,即后来举世闻名的图灵测试,最初他称之为模仿游戏。
图灵提出,若一台机器能与人类自如对话,使人类无法分辨其身份,那么在所有实际意义上,我们便可认为这台机器具备思考能力。
这不仅是一个实验,更是一种对思考的功能性定义,它点燃了心智计算理论的火花,其深远影响至今仍在哲学界激荡。
更关键的是,在那篇论文中,图灵的远见超越了测试本身。他提出了数种实现人工智能的可能路径。
其中包括“学习机器”的概念,即像抚养孩童一般,让机器通过经验积累知识,而非预设所有规则。
他还暗示,可以借鉴生物进化,利用算法来模拟自然选择的过程。
这些构想,预示了现代 AI 的几大支柱,如神经网络和元启发式搜索算法,充分展现了他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路径的深刻洞察。
遗憾的是,他未能亲眼见证自己的梦想,开花结果,汇聚成人工智能这片波澜壮阔的知识海洋。
奠基时代:20 世纪 50 年代 - 60 年代末
1956 年的夏天,人工智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。
一群顶尖学者在达特茅斯学院举办了一场研讨会,正是在这次会议上,人工智能这个术语被正式提出。
这次会议不仅是一次思想的碰撞,更是一份宣言,宣告了一个宏伟目标的启程:创造能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机器。
在早期,符号 AI 是绝对的主流。研究者们坚信,只要将人类的知识与推理能力,转化为明确的计算机规则,就能赋予机器智能。
逻辑理论家程序是这一理念最早也最震撼的展示。它能通过符号逻辑来证明数学定理,而非依赖暴力计算,这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人类的思维过程。
这清晰地表明,只要指令得当,机器确实能够胜任抽象推理。
棋类游戏也成为符号 AI 的热门试验田。极小化极大算法的应用,使早期计算机在象棋等游戏中,可以通过推演所有可能的棋局来达到最优水平。
那是一个属于自动推理器和早期知识表示的时代。人们满怀信心地认为,只要我们能穷尽所有规则,机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。
也正是在这一时期,一个名为 ELIZA 的程序,以其看似简单的设计,俘获了大众的想象力。
作为史上第一个聊天机器人,ELIZA 通过简单的模式匹配与规则库,模仿一位心理治疗师与人对话。
它常常只是把用户的话变个句式再抛回去,例如:“你说你很难过。为什么你会说你很难过呢?”
尽管原理简单,许多人却在与 ELIZA 的交谈中敞开心扉,甚至相信它真的能够理解和共情自己。
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为 ELIZA 效应,它有力地提醒我们,人类是多么轻易地会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技术之上。
ELIZA,这个纯粹由规则驱动的符号系统,却点燃了 AI 领域一个经久不息的梦想:创造出能与我们自然对话的机器。
然而,在符号 AI 一路高歌的同时,另一种思想的种子也在悄然发芽:联结主义。
这是一种早期的统计 AI,其灵感源自生物学:单个神经元虽简单,但通过精巧的连接,便能涌现出惊人的智能。
弗兰克·罗森布拉特提出的感知机,就是一种早期的人工神经网络,它被设计用来直接从数据中学习规律。
最初,人们对此兴奋不已。这些「学习机器」似乎提供了一条无需预设所有规则,便能通往智能的捷径。
这无疑是经验主义思想的体现:知识源于感官与数据。
可惜,好景不长。两种路径很快都遭遇了瓶颈,未能从玩具问题走向更广阔的应用。
符号系统虽然在特定领域表现出色,但其天性脆弱。它们难以处理常识,也无法适应规则之外的新情境。
而感知机也撞上了理论的天花板。1969 年,马文·明斯基等人的著作深刻地指出,单层感知机甚至无法处理最简单的非线性关系。
无论连接多少神经元,其复杂性都无法得到根本提升。
随之而来的,便是第一次 AI 寒冬。最初的宏大承诺落空,导致资金与公众热情急剧冷却。
而这场规则与模式、符号与统计之间的早期交锋,也为整部 AI 历史的动态演进埋下了伏笔。
知识时代:20 世纪 70 年代 - 90 年代中期
走出寒冬,AI 并未消亡,而是重新集结,符号方法强势回归。
70 年代与 80 年代,见证了专家系统的兴起与初步商业化。
这类 AI 程序旨在模拟特定领域的人类专家,进行决策。例如,用于辅助诊断血液感染的 MYCIN 系统。
当时的核心思路,是将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,通过手工编写的规则和事实进行固化。
这些系统依靠复杂的推理引擎来应用规则,最终得出结论。
这个时代,是理性主义 AI 方法的巅峰,人们试图用清晰的逻辑结构,将人类的专业智慧形式化。
与此同时,神经网络的研究也在暗中持续。反向传播算法的普及,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突破。
它提供了一种高效训练多层神经网络的方法,使其能够学习远比以往复杂的模式,从而打破了感知机的核心局限。
然而,就在专家系统达到顶峰之时,其自身的缺陷也暴露无遗。
它们构建和维护的成本极其高昂,且极度依赖人类专家耗费心神地输入知识。
更致命的是,它们的知识非常脆弱,任何超出预设范围的微小变化,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崩溃。
于是,第二次 AI 寒冬悄然而至。人们清楚地认识到,符号 AI 虽成就斐然,却难以应对真实世界的复杂多变。
而此时的统计 AI,由于数据和算力的匮乏,也尚未准备好登上舞台。但变革,已在酝酿之中。
互联网时代:20 世纪 90 年代末 - 21 世纪 10 年代初
互联网的出现,改变了一切,人工智能也不例外。
数据,突然之间无处不在。统计方法,终于等来了它期待已久的爆发契机。
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,互联网的指数级增长和计算能力的飞跃,共同催生了数字信息的空前爆炸。
每一次点击、每一次搜索、每一张上传的照片,都汇入了大数据的洪流。这正是统计 AI 所需的燃料。
有了海量数据,几十年前诞生的统计机器学习算法,终于大放异彩。
支持向量机、决策树、集成方法等技术,从理论走向实践,驱动着真实世界的应用。
搜索引擎用它们排序网页,邮箱服务商用它们过滤垃圾邮件,电商网站则用它们为用户推荐商品。
这些问题,正是统计机器学习的用武之地。它能在海量数据中洞察微妙的模式,无需为每种情况都预设规则。
但符号 AI 并未就此消亡,而是在新的时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语义网的理念开始普及,它试图通过本体等形式化的方式定义概念与关系,将全球信息编织成一张巨大的、相互关联的知识网络。
虽然语义网的宏伟蓝图尚未完全实现,但其核心思想——将世界知识组织成概念网络——却被传承下来。
谷歌知识图谱正是这种思想的杰出代表。它将符号方法与统计方法相结合,为谷歌带来了长达十多年的搜索霸权。
也正是在这一时期,我们初次窥见了 AI 的负面影响。
YouTube、Twitter 等平台,利用纯粹的算法推荐系统,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同时,也制造出了过滤气泡与回声室。
算法不仅会放大训练数据中固有的偏见,还可能被用于加速虚假信息的传播。
这些早期迹象警示我们,即便是看似无害的应用,也可能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思维与互动方式。
这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更复杂的伦理困境,拉开了序幕。
深度学习时代: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 - 20 年代初
如果说互联网时代是热身,那么 10 年代中期,深度学习则正式拉开了大幕。
这不仅是一次进步,更是一场革命。最初的突破源于人们成功训练了远比想象中更深的神经网络。
2012 年的 ImageNet 图像识别挑战赛是历史的转折点。
一个名为 AlexNet 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横空出世,其惊人的表现,彻底碾压了所有传统方法。
AlexNet 证明了,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和算力,深度神经网络就能学习到极其复杂的特征。这是经验主义路径的一次决定性胜利。
智能,确实可以从海量数据和复杂的模式中涌现。
自此,深度学习的发展势如破竹。更先进的架构层出不穷,注意力机制等关键创新,让模型能够更精准地聚焦于重要信息。
深度学习的浪潮迅速席卷了自然语言处理、语音识别和强化学习等多个领域。
谷歌 DeepMind 的 AlphaGo 击败世界围棋冠军,便是深度学习与传统搜索算法结合的典范。
它用强大的统计方法,高效探索了围棋那对于传统符号搜索而言过于浩瀚的博弈空间。
这一时期的飞速发展,也带来了一个深刻的启示,被称为惨痛的教训。
其核心观点是:从长远看,那些充分利用计算资源(即更大的模型、更多的数据)的通用方法,往往比试图融入人类先验知识或手工设计特征的方法,更为强大和有效。
这并非要全盘否定人类智慧的价值,而是强调了融合方式的重要性。
与其施加僵化的规则,不如创造一个能让算法自行发现规律的环境。
这进一步巩固了向数据驱动、统计方法的倾斜,揭示了原始算力和通用学习算法在解锁更高级 AI 能力中的核心地位。
2017 年,Transformer 架构的诞生,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。
其创新的注意力机制,使模型能高效处理长文本,理解远距离的语义关联。
这直接催生了大语言模型的崛起,如 BERT 和早期版本的 GPT,它们展现出与人类惊人相似的文本理解与生成能力。
这一切的背后,是硬件发展的巨大推动。GPU 和 TPU 等专用芯片的出现,为训练庞大的神经网络提供了必需的并行计算能力。
同时,TensorFlow、PyTorch 等开源框架,以及 Hugging Face 这类模型共享平台,极大地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研究与创新协作。
生成式时代:21 世纪 20 年代初 - 至今
这便将我们带到了激动人心的当下。20 年代初,一个前所未有地吸引公众目光的时代开启了。
2022 年,ChatGPT 横空出世,紧随其后的是 DALL-E、Midjourney 等一系列开创性的生成模型。
这些模型能够跨越文本、图像、代码、音频甚至视频等多种模态,创作出新颖且连贯的内容。
AI 不再只是分析或预测,它在创造——正如一个多世纪前埃达·洛夫莱斯所梦想的那样。其深远影响,至今仍在不断展开。
这个时代,也让我们戏剧性地回到了由 ELIZA 点燃的那个梦想的起点。
ELIZA 依靠的是手工编码的规则与技巧,而 ChatGPT 的原理则截然不同。
它是一个纯粹的统计奇迹,从浩如烟海的数据中习得了语言的奥秘,而非遵从任何明确的规则。
ChatGPT 及其同类,代表了对对话式 AI 那个悠久梦想的惊人实现,它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机器能力的想象。
然而,历史的钟摆再次摆动,并带来了一个有趣的转折。
这些强大的统计模型,在展现惊人能力的同时,也暴露了其固有的缺陷。
它们会产生幻觉,捏造事实;它们在常识推理方面步履维艰;它们的过程往往缺乏可解释性。
这些局限性,重新激发了人们对神经符号 AI 的兴趣。目标不再是二选一,而是融合。
这个新兴领域,旨在将统计模型的模式识别能力,与符号 AI 的逻辑推理和结构化知识结合起来。
我们可以用符号知识来“校准”大语言模型的输出,确保其事实准确性;也可以用逻辑规则来增强 AI 系统的鲁棒性与可靠性。
符号与统计 AI 之间的历史博弈,正在演变为一场对有效综合的探索,其目标是创造出真正大于各部分之和的、更强大的智能。
结论
我们回顾了数十年的雄心、突破与反思。我们看到的是一场两种强大思想之间的动态舞蹈。
一方是符号 AI 精确、基于规则却刻板的逻辑;另一方是统计 AI 灵活、基于模式却不可靠的直觉。
这场舞蹈,深层次上反映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哲学张力。
今天,AI 正站在一个迷人的十字路口。尽管纯统计系统已取得辉煌成就,但其固有的短板也愈发明显。
这使我们得出一个关键的认识:AI 的未来,不在于谁取代谁,而在于如何将两者智慧地融合。
尤其是神经符号 AI 这类混合路径,正展现出巨大的潜力。
然而,在我们拓展 AI 能力边界的同时,也必须严肃面对随之而来的伦理挑战。
这些系统的强大力量带来了风险:从传播虚假信息、放大社会偏见到更复杂的问责制难题。
甚至,还包括创造真正自主的超智能实体,可能带来的关乎人类存亡的终极拷问。
通过将符号推理与深度学习的力量相结合,我们有望构建出不仅聪明,而且稳健、可解释、并真正具备常识的 AI 系统。
人工智能的历史远未终结。它是一个关乎整个文明的、仍在进行中的宏大工程。
它有潜力让社会变得无比美好,也有人相信,它可能成为我们的终极威胁。
在这个故事中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:技术专家、人文学者、经济学家、历史学家、艺术家、政策制定者……
无论如何,未来的岁月都注定会激动人心。而你,也可以成为这历史的一部分。
一键三连「点赞」「转发」「小心心」
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!
 扫码添加微信
扫码添加微信
- 点赞 (0)
-
分享
微信扫一扫
-
加入群聊
 扫码加入群聊
扫码加入群聊